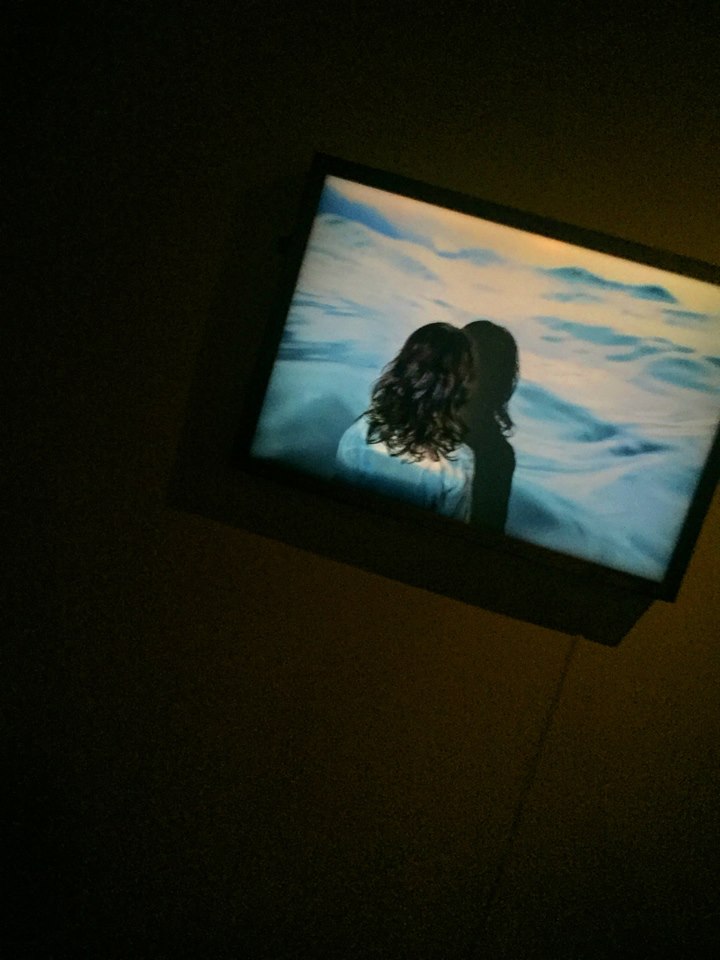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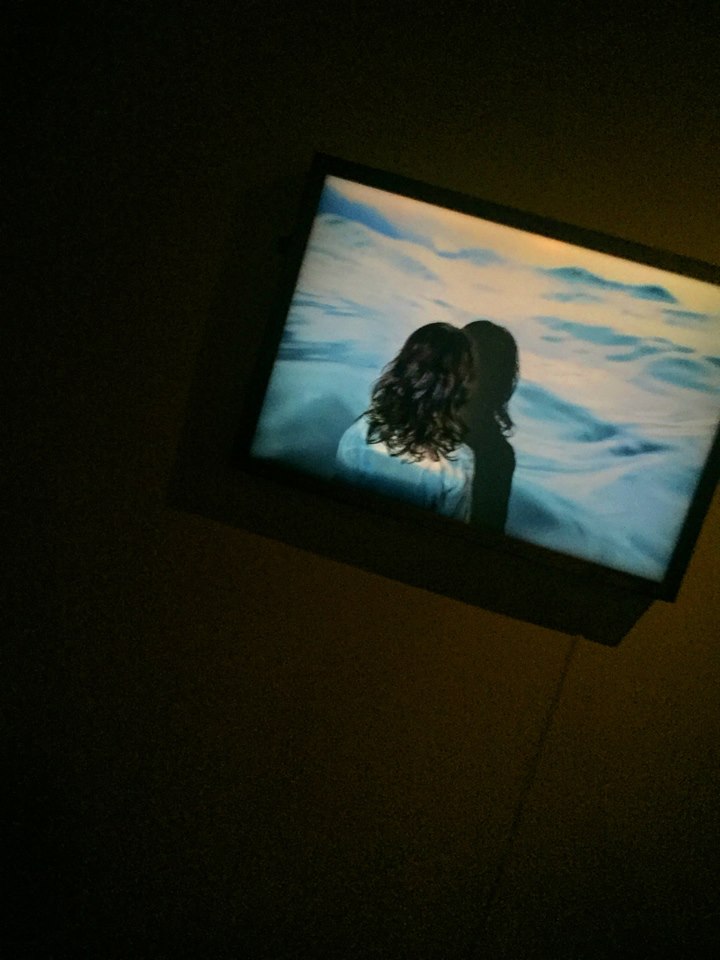
摸黑下樓
當我試著透過鏡頭,捕捉,一個美麗的風景時,眼角卻瞥見無知的路人甲,侵入我們之間的領地。下意識地側了身,想避開視線的入侵者,卻讓視角歪了。也就在這無意間按下快門,扶正了地球傾斜的角度,讓黃道與赤道再次交疊。
我一向對於攝影展有種特殊的執著,這執著不在於個人的愛或不愛,而是在於:「究竟該怎麼去看別人拍的照片?在別人的風景前面,我又是誰?」
總是不自覺會思考這樣的問題。這答案的追求不在於美學的價值判準,而在進行一種「觀看方式」的爬梳與田調:一個客觀存在的風景,在某個特殊時機下,被攝影師用了某個心情、直覺、思考….加入一段極短的機械、電子、或化學作用,在某個框框裏記錄了下來。重新檢視照片、將照片洗出來或在螢幕上秀出來、放大輸出貼在牆上展示。這一道道「程序」都是不斷「再現」的形式。究竟,在創作者主客觀的情境下,反映了什麼?抑或,在像我這樣的觀看者而言,「有沒有希望」我「看到」什麼?我想到了 John Berger 在《觀看的方式》書中提到的那種觀賞者、創作者、作品、與被描述者,四者間那種錯綜複雜的關係;也想到了安海姆在評述康德美學中,那種對於「適切性」(Suitability)的定義。
認識小光學姊也快二十年了,幾年前回交大看她的攝影展,其中一件作品令我至今印象深刻:展場中央放了一個躺椅,每個觀看者都上去躺一下,用另一個視角來仰視空中的作品。這些年,小光學姊的作品描述的對象並不是外在的風景,而是「自己」。就算畫面中是一棵樹,卻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,是那棵透過視網膜傳到大腦後,在物與心之間產生一種擴散與收斂後,於心靈底部得到的影像。因此,那已遠遠超過機械複製下的風景,而是,班雅明那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「靈光」?
無論是心象的呈現,抑或是將自己的作品投影在自己身體上,這樣像「照鏡子」的過程,赤裸裸地將內心掏出來呈現。記得自己曾經這樣做過:十八年前第一次執起教鞭,第一堂剪輯課就是放我在交大做的第一段動畫影片給學生們看,由於那是剛學會做影片的第一支作品,成品非常的粗糙、不成熟,但卻也極為真摯,不只時間精神,更投注了全副的情感進去。當時我把那段過程,以及感情上的變化,毫無保留地跟學生娓娓道來,動機就是盼望透過這樣的分享,讓他們感染藝術創作的快樂與療效,我希望他們來上這門課,不只是當作學一個軟體工具,而是可以用來抒發個人的創作管道。
那天下課時有兩個學生跑來找我討論課程內容,離去前他們對我說:「老師你好勇敢喔!居然可以在眾人面前這樣赤裸裸地把這麼深的東西呈現出來!」此後,我對於同樣如此從靈魂深處自我揭露的創作,有種「同病相憐」或是「心有靈犀」的熱愛。
就在昨天去參加小光學姊在南港的《摸黑下樓》四人攝影聯展開幕座談時,我就問了小光學姊這樣的問題:究竟學姊在這樣自我揭露的時候,有沒有考慮過觀看者的問題?畢竟這樣自我揭露其實是很不容易的,當然有人會說躲在鏡頭後、躲在作品後,透過層層符碼隱喻是安全的也是自在的。但這次小光的幾件作品中,她自己的身體跑到了鏡頭前,彷彿靈魂在那瞬間被抽離出來似的,卻又在燈箱的特殊呈現下,透視著風景中的風景。所以這樣的自我揭露,是為了希望觀眾看到被揭露的自己?還是,像後現代文學理論裡所說的「作者已死」一樣,創作完了,作者得到了靈魂的救贖,作品本身脫離了作者有了自己的生命,彼此已然毫無關係?觀眾有什麼感覺?那是他們自己跟作品之間的事,與作者無關?
不過當我問完後,就覺得其實這問題已經不再需要問。從三年前第一次回去看學姊的作品,到昨天再次看,其中的變化昭然若揭:從一個會在意觀看者角度的裝置藝術家,到一個無入而不自得的創作者。在她看到的那一刻、在她去又復返拿出相機按下快門的那一刻、在她洗出照片的那一刻、在她將照片裝置在展場牆上的那一刻、在她關上展場大燈,跟著大家摸黑上樓的那一刻……還有最後,她在我眼神中,看到我看到作品後發光的那一刻……。這每一剎那的觀照,都有靈魂,都是創作。
現在,我看著電腦螢幕上這張意外傾斜的照片,想到昨天跟小光的對話……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,在展出作品時,會不會在乎觀賞者的觀看角度?於是,從她的反應我明白了,或許直到像小光學姊這樣,自己也成為觀看者之一,最後真的做到不在乎的時候,或許,那靈魂底下映照著的風景,才是純粹的美麗。
葉子
《摸黑下樓》四人寫真聯展: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events/880493638770490?%3Fti=ia

